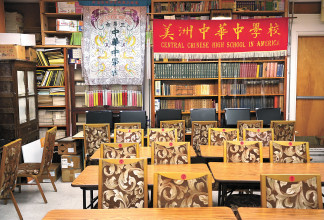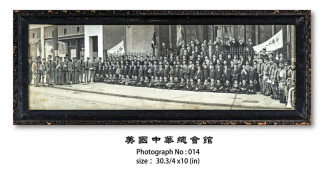文:記者陳程威
「市長羅偉如果真的要決定削減我們的經費,我希望他能親自來體驗一天——住在散房家庭裡。我不知道他要住多久才能體會,但至少住一天,看看我們的生活有多艱難。」
戴雪艷的聲音帶著顫抖,卻異常堅定。這位華埠散房家庭母親,在6月9日三藩市移民領袖獎頒獎典禮上,與其他七位移民社區領袖一同登台領獎。對她而言,這份榮譽不僅屬於自己,更屬於千千萬萬仍生活在散房裡的家庭。「我做的工作很平凡,這個獎是我們所有移民家庭一起爭取來的。」她輕聲說道。

戴雪艷(後排穿灰色套裝)榮獲移民領袖獎,與其他得獎人一起與三藩市市長羅偉(後排中)合影。記者陳程威攝
美國夢的第一次破碎
2012年,戴雪艷與丈夫帶著12歲的女兒和6歲的兒子,從廣東移民抵達三藩市,在華埠散房落腳,選擇了2 Emery Lane有32個單位的散房公寓。「因為散房最便宜,所以就選擇了。」當她推開那扇門時,現實狠狠地給了她一巴掌。
「根本沒想到要和人共用房子,一打開門,一點傢俱都沒有,只有1.2米寬的上下鋪。孩子坐在上鋪寫作業,頭會碰到天花板。我一進門就哭了,非常後悔。」更糟糕的是,散房環境十分惡劣——衛生欠佳,如爐頭壞了、漏水、發霉等經常發生。
排隊中度過的四年歲月
丈夫與兒子睡一張床,她和女兒擠另一張,毫無隱私。更難忍受的是,15個家庭共用一個廚房——一個灶台,四個爐頭;共用兩個洗手間,每到傍晚洗澡時就大排長龍。
更糟糕的是多戶共用廁所,衛生狀況極差,「廁紙多到漫出來都沒人清潔。我女兒常常上廁所上到嘔吐,她補充道:「有些散房,是80多個家庭共用一個廚房。」
四年的散房生活,讓戴雪艷壓力暴漲。女兒正值青春期,卻要長時間憋屎憋尿。多年過去,女兒提起那段生活依然心有陰影。
夫妻關係也因教育孩子問題產生摩擦。「那段時間真的非常崩潰,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會超級難過。」
她說自己那時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才能搬出去,「我在路上看到人家的房子,就很羨慕人家有自己的房子,很羨慕人家有自己的廚房、自己的廁所。」

戴雪艷上台發表獲獎感言。記者陳程威攝
守護家園的第一場戰鬥
2013年,住客們得知許多樓宇問題遲遲沒有解決,背後原因是屋主打算出售這棟散房。屋主開始單獨和每一位住客談話,表示可以給一千塊讓他們搬走。但對這些長者和移民家庭來說,一千塊的補償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。大多數住客都團結起來,向業主表達了希望留下來的意願。
2013年11月,房地產投資公司買下這棟物業。2014年10月,住客們紛紛收到逼遷通知。
逼遷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——僅僅因為住客在窗口懸掛衣服,業主宣稱此舉違反了租約,有權趕走住客。住客開始承受來自業主的諸多騷擾以及刻意刁難,在房門外懸掛中式掛曆或貼上新年揮春也會馬上被投訴。
守護家園的決心最終戰勝了害怕被業主報復的恐懼。戴雪艷和鄰居以及一班熱心的社區人士一起並肩作戰,參加爭取權益活動,成功對抗逼遷。
從受助到助人的蛻變
通過這次的反逼遷,戴雪艷更加堅定了要守護社區、幫助散房家庭的決心。她因此認識了華協中心(CCDC)和「散房家庭團結委員會」
從此,她加入華協中心,成為散房組織員,從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。堅持為社區爭取權益的使命感在她心中扎根。過去近十年,戴雪艷鼓勵並啟發無數家庭勇敢站出來,爭取權益。
最難忘的是2017年那場「保衛住屋券」的戰役。當時,房管局突然宣布削減全市50張住屋券。對散房家庭而言,這等於斷了搬出困境的唯一希望。消息傳來時已是當天下午,聽證會當晚就要舉行。戴雪艷立刻發動組織,短短數小時內動員超過50個家庭。
「那些家庭裡,有老人、孕婦、帶著小孩的,甚至有爬在地上的孩子,大家不管多困難都來了。」
那個夜晚至今深深烙印在她記憶中:「我記得有一位阿公講到激動落淚,還有青少年講著講著哭了出來。原本坐在上面的委員們一開始表情很冷淡,到後來聽著聽著,頭都低了下去。」
她停頓片刻,語氣堅定:「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被我們打動了,但最後——50張住屋券,全都保住了。」
此後,她積極參與2018年的C提案、去年G提案的推動,讓眾多居住在環境惡劣散房的家庭,能夠有機會遷出並改善生活條件。疫情期間,當很多人不敢出門時,散房家庭聯合會的住戶們還出來做志願者,幫忙派餐。

戴雪艷(左)積極參與組織散房家庭。華協中心提供
新戰役:預算削減的威脅
然而,眼下又有一場硬仗在等著他們。市府正考慮削減散房家庭團結會的預算,將直接影響住戶的權益維護與服務。「以前有些經費被砍,但今年是第一次要全部刪除,真的很難接受。」「我們正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。」
「新移民如果沒有這個團結會,連基本的社區支持都會沒有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彼此支持、更加團結,一起站出來,讓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。」
她懇切地說:「我希望市長跟市參事不要削減我們的資金。」
數據背後的人間百態
根據三藩市規劃局資料,全市約有500多棟SRO樓宇,主要集中於華埠、南市區、田德隆區,約有19,000至30,000名居民依賴SRO作為主要居所,佔全市人口約3%至5%。
自20世紀下半葉起,隨著城市更新與「清除都市敗象」(Blight Removal)政策,SRO住房大幅減少。1970年代,市重建局為興建Yerba Buena中心拆除了約4,000個SRO單位,另有數千單位因重建Embarcadero與西增區(Western Addition)而遭拆除。1989至2002年間,業主共自行拆除6,086個SRO單位,另有超過1,700個單位毀於火災。
目前全市有377棟私人SRO、121棟非營利SRO,平均月租金為918.33元。這些樓宇多數空間擁擠、設施老化、火災風險高。平均每層約有15至20個單位,住戶需共用1至2間衛浴與廚房。房東未盡維護責任、租戶權利意識薄弱,加上公共政策資源有限,令不少家庭長期陷入住房困境。
在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,是像戴雪艷一樣的千千萬萬個家庭,他們的掙扎、希望與堅持,構成了這座城市最真實的底色。
如今,戴雪艷已搬離散房,從受助者轉變為社區組織者,她曾帶領32戶家庭成功抗拒2 Emery Lane散房逼遷行動,積極參與各項住房提案,持續為低收入新移民家庭發聲。
獲得移民領袖獎,戴雪艷感慨萬分地說:「這個獎項,不只屬於我個人,是屬於所有一路陪伴我、和我並肩作戰的家庭、組織員、鄰居、家人和朋友。它是對我們這群來自散房、深知生活艱辛的人的肯定,也是對我們『散房家庭團結會』和『樓宇條例外展計劃』多年努力的認可。」
她的聲音逐漸激昂:「這些計劃不只是服務,更是許多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資源。透過這些計劃,我們幫助了無數面對困難的家庭認識自身的權益,勇敢站出來,改變自己的生活。這些都是我們親身見證、一步一步努力出來的成果。」
但她知道,自己的使命還沒有結束。「很多家庭還困在散房裡,我會繼續爭取可負擔住房,幫助更多人。」她盼望市長與市參事們能聽見散房家庭的聲音:「如果能親自體驗一天散房生活,就知道我們多需要這筆經費,知道低收入移民家庭的艱難。」

戴雪艷(前左一)發言後與「散房家庭團結會」成員一起在市政廳合影。記者陳程威攝
一個城市的良心
6月9日傍晚,戴雪艷出席市政廳舉行的移民領袖獎頒獎禮,與其他社區領袖並肩受表彰。但她更盼望,散房家庭的故事,能透過這份榮譽,被更多人看見與聽見。
「我們的孩子坐在紙皮上寫作業,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我都會想哭。」她的聲音再次哽咽,「我希望政府不要削減經費,讓更多家庭有機會走出困境,看到希望。」
在這個被稱為「酒店之城」的三藩市,還有成千上萬個戴雪艷這樣的故事正在發生。她們的聲音,值得被聽見;她們的尊嚴,值得被守護。當我們談論城市的進步與發展時,不應忘記那些在陰影中生活的人們。戴雪艷的故事告訴我們,真正的領袖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,而是那些在最困難的環境中,依然選擇為他人點燃希望之火的普通人。
她們是城市的良心,是社會進步的真正推動者。她們的存在提醒我們:在追求繁榮的路上,不能丟下任何一個人。

戴雪艷(前排左一)帶領散房家庭抗議預算削減。華協中心提供
後記
這是一個關於尊嚴與希望的故事。戴雪艷的故事提醒我們,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,都是一大群活生生的人,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人生。當我們在討論城市政策、住房問題時,不妨想想那些在散房裡排隊上廁所的孩子,想想那些為了一張住屋券而奔走呼號的母親們。她們的聲音,應該成為我們制定政策時最重要的參考。
正如戴雪艷說:「我們不是為了自己,是為了下一代。」這或許就是一個社會能夠持續進步的根本動力——那些曾經受過苦的人,選擇讓後來者不再受同樣的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