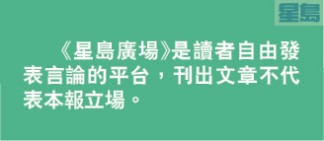余非 星島中文電台時事觀察
11月下旬,阿根廷總統選舉哈維爾·米萊(Javier Milei)當選,我撰文的這一刻,大家應該已聽過有關他的介紹,例如米萊是阿根廷極右翼的自由派人物。而最為人悉的標簽,是他被稱為阿根廷特朗普。
本文不會只從出格的政治素人這角度去談這位新任阿根廷總統,更主要的角度是,看看他接手了一個怎樣的國家,尤其一談米萊提出的美元化政策的可能性,以及當中的意義。當現在金磚國、中東也開始行去美元化的走向時,阿根廷為何要反其道而行,原因何在?我覺得很值得知道,以下跟大家一談。
首先,阿根廷此次總統選舉是國家處於艱難時期、甚至可能是經濟破產邊緣的選舉。阿根廷人在過去幾年面對不尋常的通貨膨脹,以及經濟發展乏力的局面,對執政黨的負面情緒很大。於是米萊針對經濟的出格言論,例如「炸毀」中央銀行,對受苦的民眾來說是最好的宣洩,因此贏得很多選民的支持。執政黨做得不好,罵他最容易得分。那怕將來他接手之後未必比現時的執政黨更能成事。因此,選前已有民調反映米萊會輕易取勝,可以輕鬆擊敗執政黨推出的侯選人、經濟部長馬薩。而事實上他也真的以超過對手大約10%的得票贏得選舉。
米萊在當選演講中說:「從今天開始,阿根廷要重建了。從今天開始,阿根廷的衰落結束了。」然而,一切說易行難。阿根廷是否可以重新起步?有多困難?以下且看阿根廷近幾年的債務有多嚴重。而行美元化政策,看來跟經濟原因有關。
2023年是阿根廷的大選年。這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貨膨脹率超過100%。而事實上過去兩、三年的年通脹率也超過100%。這一年,阿根廷比索在黑市兌美元的匯率已下跌了一半。阿根廷也想用印比索來應付政府開支,但加印貨幣只會加速比索貶值,以及令通脹更加惡化。當選的米萊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學家,在競選時提出國家經濟要行美元化政策(不是去美元化,是去美元化的逆流),認為阿根廷要逐漸用美元取代阿根廷貨幣比索。以下是個很值得留意的論述概念——因為近年「去美元化」這個經濟手段成了政治術語,大家很正常、也很容易將米萊口中的美元化,從政治取態的角度去解讀。因為他也真的說過不跟中國合作、擺出一副反華姿態。
總之,是與現屆政府相反。沒錯,米萊有不親華的一面;可是,「去美元化」對米萊和阿根廷來說,未必單純是政治表態,或是涉及實質的、經濟和貨幣角度的考慮。因為不少拉丁美洲,也即是南美洲國家,出於被動也好,不得已非用不可也好,有其美元化的歷史過程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
舉例,厄瓜多爾、薩爾瓦多和巴拿馬等國家,都行美元化貨幣政策。不過這些算是拉美的小國,阿根廷卻是拉美的大國,在經濟總量上(先不理他的國債)是拉美前三大經濟體系。如果他也行美元化的方向,對美元來說,不是一件小事。阿根廷和美元曾有一段離離合合的曲折經歷,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。總之,如果日後又再行美元化政策,是走回頭路。從中反映,比索撐不下去了;反之,美元在濫印之下死不去。
我在之前的節目內已提過,誰也沒料到俄烏之戰,其實是俄美之戰,傷得最重的是歐洲和歐盟。詳情已多次談過在此便不重覆了。簡言之,是斷了俄羅斯能源之後,歐洲能源供應不穩和價格上升,令不少企業,尤其是德國一些很有根基的工業離開德國,部份去了中國,更多是去了美國。而吸夠歐洲實業的血之後,美國又用高價液化天然氣為歐洲「解困」,堂而皇之搶錢。美元,靠吸歐盟血復活。當中馮德萊恩是最大功臣。在美元沒有崩潰的背景下,阿根廷行美元化,是其經濟和生存角度的考慮。因為美元沒崩潰,仍然成為部份國家依賴的貨幣。
以厄瓜多爾為例,當年官方採取放棄本國貨幣蘇克雷(Sucre)改用美元時,被認為是激進的做法,但今天一切在厄瓜多爾也習以為常。因為蘇克雷已貶值至買不到東西。而行美元化後,他們的經濟不是因此而好轉,一樣是負債高的國家,可是當中那種衰弱,是穩定地衰弱;於民間而言,起碼有一種可以買生活必須品的貨幣。其他拉美國家如巴拿馬、薩爾瓦多,以及東南亞的東帝汶也使用美元,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。只可以說,於從前,用美元,對部份其本國貨幣不斷貶值的小國而言,是沒有選擇之中的選擇。